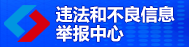三流導演讓他們的主角隨手拿上一本書作道具,二流導演以閱讀口味彰顯主角的身份和性格,對一流導演來說這卻是價值觀層面的事:他們每選擇一本書都埋下一個彩蛋——你讀什么,決定著你應該上天堂還是下地獄。
一個值得津津樂道的例子是李安埋下的伏筆。
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開場前30分鐘里,李安讓他的男主角依次讀了4本書:印度神話《黑天》、儒勒·凡爾納的《神秘島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地下室手記》和阿爾貝·加繆的《局外人》。
四本風格截然不同的書,同時疊加在同一個人身上,就有些意味深長了。《黑天》講的是印度教主神毗濕奴第八個化身的故事,它是派最早接觸到的印度教知識,當黑天“一張口看進去就是整個宇宙”時,派的世界觀就此形成,信仰的力量支撐著他此后在海上的日夜。凡爾納的《神秘島》培養了少年派的科幻素養,也暗示著他人生即將遭遇奇跡,為什么不相信呢?他后來真的踏上了神秘食人島。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始于派對學校教育感到厭倦之時,也是在他目睹了老虎食羊的慘劇之后,被視作存在主義代表作的《地下室手記》,不僅為派的離奇經歷找到了合理的解釋,也是電影主題的靈光一現:人的存在即是荒謬的。
而存在主義大師加繆的《局外人》(電影中譯做《異鄉人》)呢?更像是導演和他的主角之隱秘的呼應。李安那句廣為流傳的語錄是這么說的:“我從來都不是什么地方的公民。我的父母離開了大陸,來到臺灣,在那里我們是局外人。然后,我又來到了美國,仍舊是局外人。當我重新回到了中國大陸的時候,我又變成了一個來自美國的局外人。”
無處不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
這不是李安的電影里第一次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。20年前的《飲食男女》里,鐘國倫在麥當勞外等待打工的女友,靠在摩托上讀一本《白癡》,被問及是什么時,他酷酷地回應:“陀思妥耶夫斯基。”你可以把這視作是青春期敏感孤獨的象征,當然也可以僅僅是青少年的裝逼神器。在李安的回憶中,他本打算讓鐘國倫讀米蘭·昆德拉,是被制片改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。
侯麥1986年導演的那部《綠光》里,女主角在巴黎車站和男主角邂逅,也是多虧這本《白癡》才搭上話的。而在1969年的《幕德家的一夜》里,侯麥的男女主角整晚談論的則是帕斯卡爾的哲學。1992年的《冬天的故事》里,他又讓主角們重溫了一把莎士比亞。
伍迪·艾倫的電影《賽末點》里,男主角也要讀陀思妥耶夫斯基:電影開場不久,從愛爾蘭到倫敦當網球教練的窮小子威爾頓,被安排躺在床上讀一本《罪與罰》。這是伍迪·艾倫向陀氏致敬的小趣味,也暗示著男主角宿命般的輪回:從那一刻起,他注定要像書中的主人公殺死房東姐妹的機緣巧合一樣,蓄意殺死情婦之后再偶然殺死她的房東。悶騷的伍迪·艾倫持續對紐約知識分子進行嘲諷,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然是最佳選擇。無論是早期的喜劇電影《愛與死》(1975)中被判處死刑的士兵、《罪與錯》(1989)中聘請殺手干掉情婦的名醫,還是后來《獨家新聞》(2006)與殺手相愛的女記者、《卡珊德拉之夢》(2007)中兄弟間的殺戮,始終能找到無處不在的《罪與罰》中道德審判的痕跡。
《罪與罰》有時候也是一條愛情線。2009年的短篇集《紐約,我愛你》中,巖井俊二讓自己的男主角奧蘭多·布魯姆被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和《罪與罰》折磨得不勝其煩,最終和他電話傳情的女主角帶著一本《罪與罰》來到他家時,他問:“書看完后,是不是我就得娶你?”上世紀80年代那部《上海灘》里,趙雅芝飾演的馮程程問:“你讀過《罪與罰》嗎?”周潤發答道:“過去看過,不過都忘了。”很多人是因為這一幕才對比起了許文強和拉斯柯爾尼科夫在“殺人”這條路上的殊途同歸。而最近大熱的日劇《完美的離婚》里,女主角決定和男主角離婚,在深夜的拉面店里自顧自地吐槽:“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寫的《罪與罰》那本小說嗎?我看過哦。因為聽說我老公畢業論文寫的這個,我覺得看了能更了解他吧,就買了上下卷。我以前沒看過這么厚的書,里面還盡是些晦澀的語句,讀上卷的時候覺得很受挫,可是讀下卷的時候,把我感動壞了。我一邊哭一邊告訴他:我終于可以跟你分享一樣的感動了。然后你知道他說了什么嗎?他說巖波文庫出版的《罪與罰》,不是上下卷,而是上中下三卷——你把中卷漏掉了。”
當《生活大爆炸》還在對《暮光之城》吐槽時,《迷失》早就出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,更以一場“你知道海明威很妒忌陀思妥耶夫斯基嗎?”的討論,暗示著主角之間的對立關系,你要等到大結局時,才發現這里埋著一個劇透的伏筆。《迷失》的另一個創舉是:導演讓主角讀一本名叫《壞雙胞胎》的驚險小說,講述的是一個生物制品公司的大陰謀(《迷失》劇情中的幕后指使就是一家名叫“達摩”的生物制品公司),劇集播出期間,電視真的將這本架空的小說變成了出版物,封面上赫然寫著:“他在坐上‘815航班’之前的最后一本小說。”
“俄羅斯文學三巨頭”的另一位,列夫·托爾斯泰也是電影主角們的心頭好。《荒野生存》中,男主角最摯愛的書是《戰爭與和平》,最終也是《家庭的幸福》中那段話讓他頓悟了生命的意義:“我曾經歷了許許多多,現在,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是幸福,在鄉下恬靜的隱居,盡可能對人們做些簡單而有用的善事,盡管那些人并不習慣我為他們做了這些,做一份真正有用的工作,最后休息,享受大自然,讀書,聽音樂,愛周圍的每一個人。這就是我對幸福的詮釋。在這些之上,有你為伴,也許還有我們的孩子,一個男人還能再渴望些什么呢?”而在凱特·溫絲萊特主演的《朗讀者》中,和《奧德賽》、《荷馬史詩》、《老古玩店》一起,這本《戰爭與和平》也出現在男孩為她朗讀的書單中。
對中國的觀眾來說,還有一本著名的俄羅斯著作: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《演員的自我修養》——這就是周星馳的功勞了。
當主角在戀愛的時候他們在讀些什么?
1995年,巖井俊二在電影《情書》里普及了一把普魯斯特,柏原崇一襲白衣靠窗而立,那模樣成為了萬千少女心中的完美情人,而他和中山美穗之間兩個藤井樹的隱秘愛情線索,就藏在一本《失われた時を求めて》中——再沒什么書名比“追憶似水年華”更適合用來總結無疾而終的初戀故事了,不是么?
不少觀眾在囧瑟夫主演的那部小清新愛情片《和莎莫的500天》中,找到了阿蘭·德波頓的小說《愛情筆記》的痕跡。而囧瑟夫參加女主角的家庭聚會時,送給她的是阿蘭·德波頓的另一本書:《幸福的建筑》。這本書屢屢出現在囧瑟夫的閱讀場景中,并非只是導演單純的致敬,更是一種暗示:一個靠寫賀卡祝辭謀生的窮小子,始終沒放棄想要成為建筑師的夢想。
被稱作“美國版呼嘯山莊”的電影《冷山》,女主角艾達最愛的書的確就是《呼嘯山莊》,當要表達對男主角的思念之情時,她選擇向女仆念出了這本小說里的經典段落:“我對林頓的愛,就像林中的樹葉。我很清楚,當冬天使樹葉發生變化時,時光也會使葉子發生變化。而我對希斯克里弗的愛,恰似腳下恒久不變的巖石,它雖然給你的歡樂看起來很少,可是必不可少。”
劉德華和鞏俐主演的《我知女人心》里,兩人第一次見面,鞏俐脫手掉在地上的書是法國作家妙莉葉·芭貝里的《刺猬的優雅》。而在電影版《刺猬的優雅》里,女主角——她不過是一個肥胖的門房——讀的卻是谷崎潤一郎的《陰翳禮贊》和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根據米蘭·昆德拉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《布拉格之戀》中,女招待特蕾莎,讀的也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
當主角們戀愛的時候他們在讀些什么?1995年的《愛在黎明破曉前》,女主角塞琳娜讀的是法國作家喬治·巴塔耶的《愛華坦夫人及其它》,男主角杰西讀的則是演員克勞斯·金斯基的自傳:All I Need Is Love。1999年的《諾丁山》,男主角在自己的書店里向女主角推薦的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·帕慕克的《伊斯坦布爾》,這本書5年后出現在了《BJ單身日記2》里。2001年的《緣分天注定》,女主角把自己的地址寫在一本二手的《霍亂時期的愛情》扉頁中,男主角在十年中每逢舊書店必進,只為了尋找這本書的蹤跡。2006年美國版《觸不到的戀人》,女主角最愛的一本書是《勸導》,她把簡·奧斯汀視為愛情導師:“她告訴我們愛情需要等待”。2009年的《單身男子》中,英語教授喬治在一堂課上向學生們講起了赫胥黎的《長夏之后》,而當他和同性男友吉姆坐在沙發上看書時,讀的是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和杜魯門·卡波特的《蒂凡尼的早餐》。
跟著電影去讀書
有時候,主角讀什么書,是導演的解謎線索,比如大衛·芬奇在《七宗罪》里安排的那本《神曲》。在他2007年那部《十二宮》里,出現的則是密碼愛好者的必備——美國情報專家戴維·卡恩的《破譯者》——1967年精裝版。在他2011年的《龍文身的女孩》中,主角讀的書則變成了瓊·狄迪恩《充滿奇想的一年》、庫爾特·馮內古特的《沒有國家的人》,以及鮑比·菲舍爾的“國際象棋圣經”:《難忘的60局》。
美軍上校讀什么?在《現代啟示錄》里,馬龍·白蘭度的案頭書籍是弗雷澤的人類學奠基之作《金枝》。匈牙利伯爵讀什么?《英國病人》中,一直陪伴在男主角身邊的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。香港教師讀什么?張學友在《男人四十》里讀的是一本《萬歷十五年》。古董書商讀什么?《第九道門》里,約翰尼·德普一開場就騙到一套1780年的初版《堂吉訶德》。叛逆少年讀什么?英劇《皮囊》第一集里,男主角托尼坐在馬桶上讀薩特的《惡心》,他愛讀的書還有:珍妮特·溫特森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和尼采的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。
別以為科幻片的主角就不讀書。
美劇《隕落星辰》中,人類反抗軍撤退時,主角在《雙城記》和《海底兩萬里》之間猶豫良久,現實還是幻想?他最后決定帶走比較輕的那一本。
2012年上映的《全面回憶》中,男主角在上班時讀著一本破舊的小說:伊恩·弗萊明寫的“007系列”之《007大破海底城》。讓一個被洗腦后的特工讀一本特工小說,以此完成對他身份的暗示。這還只是小伎倆,一流的導演會讓黑客讀哲學。
沃卓斯基兄弟在《黑客帝國》的一開頭,選擇讓基努·里維斯把非法軟件藏在法國哲學家讓·鮑德里亞的《模仿與擬像》中,而他打開的那一頁,赫然寫著:“論虛無”。《黑客帝國》直接導致了哲學家們樂于用鮑德里亞的學說來論證《黑客帝國》是對現代商業化、媒體化社會的寓言。鮑德里亞則在一次采訪中說:“《黑客帝國》把‘真實的荒漠’這一哲學命題做到了極致——機器設備的擴張不可阻擋,人類要么在數字化的系統里被數字化,要么被系統拋離到邊緣。”
有時候,同一本書到了不同主角手上,也會遭遇天壤之別的命運,這是一個哲學命題。比如同樣一本《圣經》,在肖申克手上它暗藏自由之道,而到了《美國派》那里,也只能充斥著青春期特殊的荷爾蒙氣息了。
上一篇: 單位小職員 裝逼守則
下一篇: 滬膠:供需壓力有增無減,后市跌勢未改
 滬公網安備 31011502005575號
滬公網安備 31011502005575號